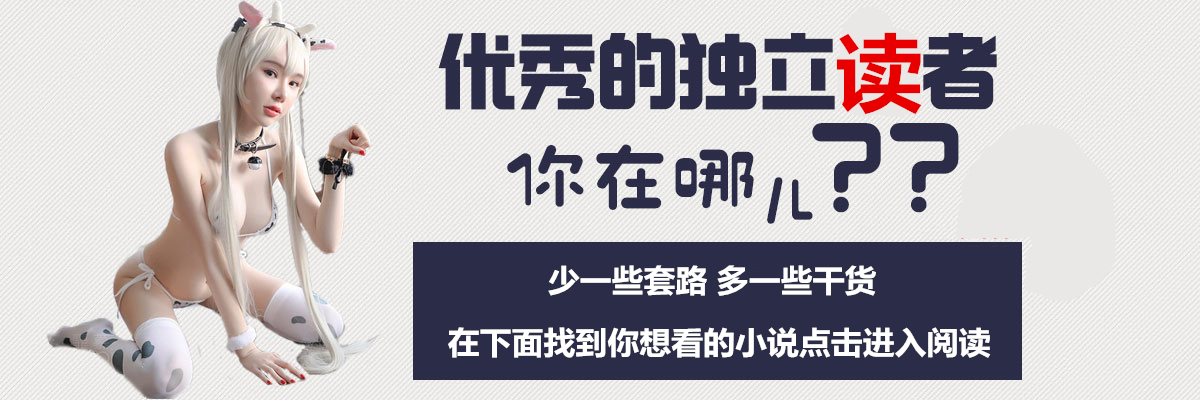这么敏感的电影居然上映了!这一次,希望它能火得更久一点
虚谷万等,电影院终于复产了。
而在暑期档首批公映电影成员名单中,出现了第一部题材相当脆弱的自然主义电影作品——《可恶逃亡者》。
作为中国第第一部高度关注被性侵幼儿初生后存活现况的电影,《可恶逃亡者》的难能可贵在于,它并不著眼于性侵该事件当今社会的激烈来吸引网络流量,而是让整个社会高度关注到性侵给被害者带来的,是多么巨大而长久的危害。
当被害者不需要在未来艰难的光阴中独自一人舔舐喉咙,儿时的阴霾才有走出来的可能。
遭受性侵
是永久性的危害
电影取材自真实世界该事件,以两个男孩的视点来讲诉。
昙生和宋曲枝,九岁时都曾遭受过初生女性的侵犯。有着同样遭受的两人,在初生后,却产生了迥然不同的感情态度和存活抛物线。
昙生优先选择半封闭他们。
她憎恶母亲,仇视女性的亲密无间接触,故意模糊不清异性恋特征,狂热练拳击,只为有一天能向儿时加害者报仇。
而宋曲枝优先选择了放荡他们。
她斗智斗勇于各式男人之间,默默地在性行为上狂热罪恶,默默地又身陷「被害者羞愧」之中。
她觉得他们脏,没错得到爱情,把遭受侵犯看做是他们除去科紫麻的「犯罪行为」。
婚姻制度的拘禁,儿时恶梦的冲刷,加上友善鬼神的憎恶,让宋曲枝人格鄙视的情绪逐渐达到顶峰,最终,她优先选择在浴缸中结束他们的生命……
这两种极端的心理状态不是艺术加工,更不是个例。
现实生活中,很多九岁遭受过性侵的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会陷入严重的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
抑郁,焦虑,自残,甚至是自杀。
还记得甘肃坠楼男孩小奕吗?
因为被班主任猥亵,她患上抑郁症和创伤性应激障碍。尽管接受了无数次心理疏导,还是无法从那段恶梦般的经历中挣脱出来。
两年时间里,她多次尝试自杀,3次服药1次跳楼,都被救了回来。
最后一次,哪怕消防员已经攥住了她的手,她还是挣脱了,纵身从8层楼高的商场窗台上跳了下去。
鲍毓明性侵案的被害者李星星,同样无法摆脱心理上的障碍。
自14岁起,鲍毓明开始圈禁性侵她,强迫她观看未初生色情片。为了让他们的行为合理化,鲍毓明还不断用男孩的用处就是用身体取悦男人这样的观念给她洗脑。
长时间处于被控制的、极端无助的环境里,李星星开始出现对鲍毓明的各种反复与依赖的混乱情绪。
她在日记里写:我逐渐感觉他们病了,我对一切都不再相信,甚至觉得我最在乎的身体的各种器官,我所珍爱的各种爱好和特长,都不在我身上,而在他身上。
日渐加深的人格怀疑和鄙视,让她多次自残,并企图跳海自杀。
台湾作者林奕含少女时期曾被家教性侵,这段经历也成了她走不出的恶梦。
27岁那年,她写下自传体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自杀身亡。那本书中有一句话,我时至今日仍记忆犹新:
其实我第一次想到死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人生如衣物,如此容易被剥夺。
被性侵不等于「一辈子被毁」,但被害者若得不到救赎,伤痛真的会伴随一生。
荡妇羞辱
不异于二次凌迟
毁掉被害者的,有时不是性侵本身,而是社会舆论的偏见和歧视。
惯会使用「荡妇羞辱」的人,可以轻易地和犯罪者产生共情,却无法对被害者报以最简单的尊重。
知乎上,曾有一位匿名博主讲诉了他们九岁时遭受性侵的经历。
那时,她才3、4年级,被一个老爷爷强奸了,她的爸妈毅然优先选择了报警。
在坏人被绳之以法后,她重新回到学校上学。没想到,嘲笑和羞辱纷至沓来。
学校的同学会故意问她,是不是被强奸了,有些同学甚至会把「老爷爷」当成一个梗,用怪异的语调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出来,然后一大群人开始哄笑。
恶意的讥笑,没完没了的非议,逼着她只能转学。
可很快,新学校又传开了她被强奸的事情,隔壁班的同学会组团跑到她的教室里围观她,指责她干了这么丢脸的事还好意思来上学。
邻居们也把这事当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她和家人仿佛成了周身污秽的耻辱鬼神,被四周或好奇、或歧视的目光层层包围。
周遭的恶意给她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霾,以至于她初生后仍不敢社交,不敢恋爱。看到年纪大的女性,会条件发射地恐惧,喘不过气,整晚整晚地做恶梦,频频梦见被陌生男人跟踪。
传统贞操观念和被害者有罪论,就像是一道天堑,把她阻挡在幸福的门外,她只能如同罪犯一般卑微、小心地活在阴霾里。
多么讽刺,明明犯罪的是加害者,到头来人生孤苦伶仃、充满阴郁的,却是受害人。
可是,当被害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加害者却可以轻易摆脱道德舆论的谴责,这样的世界,该多令人失望?
高度关注性侵案
应当是全社会的共识
鲍毓明该事件曝光后,有网友鼓起勇气发了一篇长微博,讲诉他们小时候被表哥以做游戏的名义性侵的经历。
微博发出后短短几个小时,她竟然收到了上千条私信,全是年幼时遭受过性侵犯的人讲诉他们屈辱的回忆。
而对他们实施侵犯的几乎都是身边的人:继父、爷爷、姥爷、邻居、堂表哥、老师,甚至是亲生父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少年幼儿研究中心主任童小军曾经说过,九岁时被信任的大人侵犯过的孩子,更容易消极看待他们,认为是他们导致了性侵发生。在孤立无援又极度痛苦时,甚至会主动合理化性侵者的犯罪行为。
初生后,他们仍会陷入抑郁、自责、羞愧的复杂情绪中,拒绝向外界倾诉和求助。
这些孩子承受的痛苦,往往是更长久的。
一个孩子的最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就是家庭,但这类案件中,家庭不仅没有监护的、保护的作用,反而造成了危害。
针对日益严峻的未初生性侵问题,国家也一直在努力。
2019年12月,最高检提出试行未初生人性侵案件「一站式取证」:接报未初生人性侵案件之后,公安机关刑侦、技术鉴定,检察机关等部门同步到场,一次性开展询问调查、检验鉴定、未初生人权益保护、心理抚慰等工作。
这项措施,既是出于对未初生人的心理关爱和隐私保护,也避免了反复问询案件细节,对未初生人造成二次危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公布了一条新规:未初生人遭受性侵犯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即遭受过性侵犯的未初生人,初生后仍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主张他们的权利。
而作为家长的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首先,正视未初生人性教育。
教育家方刚曾说过:性教育不是简单的生理知识教育,它是人格成长的第一部分,是一个人生观、价值观、责任感全面成长的教育。
孩子如果什么都不懂,他们靠什么来识别危险,保护他们?
这世界上好人确实占多数,但坏人遇到一次,就足以毁掉一生。
其次,改变观念。
被性侵并不可耻,可耻的是那些实施性侵的人。
当被害者勇敢发声,抱团抗争时,我们要做的不是窥探他们的隐私,不是质疑他们的目的,更不是粗暴地施以荡妇羞辱,而是告诉他们:你可以不原谅危害你的人,但请原谅他们,你并没有错。
最后,建立共识。
声援每一个被害者,哪怕他并不「完美」。
支持严惩每一个性侵犯,哪怕他有天大的苦衷。
要记住:保护我们孩子的最佳方式,是保护所有的孩子。
○ End ●
推荐阅读
-

?宝马新5系配置详解!这17款车型你最想入手哪一个?
-
黑龙江省290农场一天比一天热这钱真不好挣是用汗水换来的哎
{{if!data.isVip&&data.isActText}}{{elseif!data.isVip...
-
黑龙江干流堤防290农场段再次出现溃口
本报记者从吉林省水利厅水利厅司令部了解到,继16日再次出现宁远河后,27日7时,吉林河段堤防290农庄段悲剧重演宁远河。历经三个多...
-
黑龙江农险冰火两重天地方财力不足致补贴不一|农业保险|农险|财力
位于中俄林密吉林沿线的集贤县五原镇东方村今年遭遇洪水侵袭,许多农农作物受灾地区,农民周俊民种的200亩小麦几乎无人问津。幸好他参与...
-
黑龙江农垦290农场大雁繁育基地成为湿地生态养殖亮点
【编者按·中国军用养殖业网】日前,农牧一八〇农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不远处,1500万头毛发亮光、身形丰满的雁在大坑里无拘无束地玩耍,...
-
鲜为人知的“料罗湾海战”——晚明与荷兰的战争
事件起因国内背景明崇祯时期,受小冰河期影响。中国北方长年干旱、中原和东部数次特大地震、北方瘟疫流行。除江浙闽粤一带受灾影响后仍然恢...
-
魏县关于进一步调整疫情封控管控措施的通告
肥乡县禽流感防控工作工作组办公室关于更进一步修正禽流感封控管控举措的通告各阶层农村居民:为统筹推进禽流感防控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
-

高职高考2022年可报考院校及最低录取分数线
-

高尿酸常常没有症状尿酸高可致痛风肾病和结石
-
高一学生举报老师教师节强制收礼:教师节,你准备送礼吗
立刻就要到此日了,每月那个时期,小学生家长们都心里感到恐惧,特别是新升学的小孩小学生家长,不晓得要千万别给同学赠礼,也不晓得新幼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