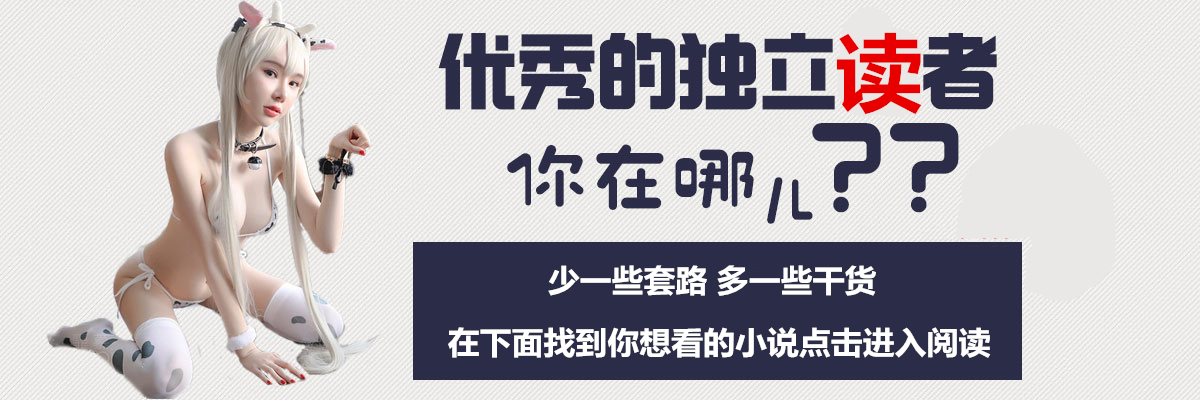王拥军就任天坛医院院长,他写的第一份病历,曾被主任扔出窗外
默氏人事变动。
在中国医生节的前一晚,8月18日下午, 天津市疗养院信息中心党委委员、秘书长潘苏彦,组织与老龄管理所处长王勇来到默氏,宣布了区委、市政府决定:王安民同志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独立设置默氏主任(正处级)。
对此,王安民在讲话中表示,默氏从大高职小综合性产业发展为强高职大综合性,逐步向科技型疗养院、综合性性疗养院产业发展,是历史突显的新责任。未来在坚持脊髓学科专业特色领头的同时,推动疗养院全面产业发展,再创新光辉。
图片来自天坛疗养院官方网站
在中国脊髓病学领域,王安民是领头羊,前任外科学脊髓病学商会秘书长委员,在卸任天坛疗养院主任之前,他已经担任天坛疗养院副主任多年。
虽然现在已是徐显秀的大专家,奥波切茨安民的脊髓高职医生的生涯第二局并不顺利。2017年,他在中央电视台电视节目《主讲啦》中,以《为什么要做优良的医生》大篇幅,讲诉了他早年生涯。
第一次写检查单,被秘书长丢出窗前
1982年8月,王安民大学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农学系,八岁时,他刚刚20岁,分配的专精并不是脊髓外科,大内科秘书长真的他的脑袋松省,替他选了脊髓外科,因为那个学科专业昂西桑县,彼时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不愿意选那个处室。
到了脊髓外科,王安民写的首份检查单就被秘书长丢出了窗前。十多个大夫看着我,一个幼年时代的年轻人,心里受的打击是十分大的。的确是我并谓了,的确是检查单写得不对,所以彼时我印象十分深刻,流着眼泪出去捡半生检查单。
救活检查单后,他也实在看不出来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等大家都乐县房走了,秘书长到他旁边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千万别误以为我扔你的检查单使你十分羞愧,你千万别误以为上面错了几个字就是几个字,他说你知道有可能这一行字换得的是一条心灵。
秘书长的这句话是王安民爱好那个专精的已经开始,让他真的那个业余离心灵这么近,他真的自己的业余一下变得高尚起来。从那天已经开始,他下定决心留在那个专精,一干就是近40年。
成为脊髓外科医生的第二年,王安民就遇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病例。
那是一个15岁的少女,三个月前已经开始四肢无力,被送到疗养院时已经四肢瘫痪,做了各种检查都不知道是什么病。王安民给那个少女做了个活检,在显微镜下观看,虽然看着不正常,但他完全不能判断。他又到旁边的医科大学,用医科大学的电子显微镜看,依然看不出来名堂。
那时候,他知道北京301疗养院有位老专家叫黄克维,是中国脊髓病理的最高权威,所以下了夜班后,他坐了4个小时火车到北京,把片子带给黄教授看。
黄教授让学生复印了厚厚的一大本英文文献给王安民,看完文献后,王安民知道了这是一种十分十分特殊的疾病,叫线粒体糖原脂质累积病,此前中国从未有过关于那个病的报道,他是首个发现者。
找到了病因,经过治疗,三个月之后,那个孩子重新回到了学校。从那个病例,王安民明白了医生的每一步努力,可以使一个枯萎的心灵重新绽放,这也是医生的最大价值。
带领天坛疗养院登顶脊髓病学的高峰
1989年,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髓病学专精硕士大学毕业后,王安民进入北京宣武疗养院工作,之后他到美国阿肯色大学医科大学做了近两年博士后研究。2000年,默氏向他发出邀请,他果断选择了回国。
那时候天坛疗养院的脊髓内科只有一名硕士生导师,一个博士,全科的科研经费只有32万,没有人发过SCI,几乎没有医生会看脑血管病。
接手之后,王安民先从学科专业建设入手,把疗养院的会议室改成临床研究中心,把疗养院的招待所改成脑血管中心,2001年就建立了国内第一家标准化卒中单元。2002-2005年完成了天津市组织化卒中防治系统的研究,在全国展开卫生部中国卒中中心培训项目的研究及实施。2006年以来重点从事脑血管病转化医学和脑血管病医疗质量促进;主持成立卫生部脑血管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启动脑血管病诊疗技术规范化应用金桥工程。
在王安民的带领下,默氏如今早已立在国内脊髓病学领域的金字塔尖,他曾经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尚校长保证,在他退休之前,会努力保住天坛疗养院第一的位置。
把医生分成四类
在王安民眼中,医生可以分为四类。
最低级的是不合格的医生,或者是培训中的医生,他以自己为例,当年他大学刚大学毕业,检查单被秘书长扔了出去,那时候的他就是不合格的医生,因为还不能保障患者的安全。
比不合格医生再高一个段位的,是合格医生,能够按照指南、按照教科书和上级医生的指导循规蹈矩地看病。
更高一个层次的医生,王安民称之为优秀的医生,能从临床中总结经验,能个体化的进行诊疗,这样的医生的患者预后也往往比别的医生更好,每个患者都希望遇到优秀的医生。
而在王安民的名单中,排在第一的是优良的医生。除了能为患者解决好问题,还能创造新的理论,新的治疗方式,新的学说,让更多的病人获益。
他表示,中国现在有很多优秀的医生,但是缺乏优良的医生。
未来的中国医疗要强基层
王安民一直记得,2006年10月29日的那天傍晚,他一个人坐在家里的落地窗前,没有开灯,紧张的等待着2012年的世界卒中大会举办地的票选结果。
然而最终的结果让他十分失望,北京没有能够获得主办权,一位德国教授告诉他,虽然北京的会议条件很好,但中国脑血管病研究的成绩却不为世界所知。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中国跟世界走在同一起跑线上。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科技创新对健康的支撑作用描述,让王安民感同身受,因为没有新的科技手段,没有新的研究,没有新的证据,脑血管病的防控永远在困惑中打转。所以他在演讲中呼吁,更多的优良的医生去参与研究,找到新的治疗方法,使中国的1100万脑血管病人早日摆脱痛苦。
王安民对《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第二点体会是,未来的中国医疗要强基层,因为大多数病人都在基层。
有一年王安民和同事到了甘南,他们在当地一家养老院里待了整个下午,分别问40位老人,知道自己的血压吗?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老人平均年龄约70岁,从未量过血压,也不知道自己会有脑中风的风险,甚至都没听过那个词汇。
经过检查,王安民发现有5位老人脑袋里已经出现了病变,未来几年可能会得中风。
有个姓王的老人,王安民至今还记得他的样子,整个下午,他走到哪里老人跟到哪里。当他坐中巴车离开时,他坐在最后一排,回头看见老人在跟着车跑。
王安民说那时候他心里十分难受,他知道基层这些高危人群多么需要去关注,所以强基层对于实现健康中国十分十分重要,这不仅是口号,更需要行动。
来源:医学界
作者:田栋梁
校对:臧恒佳
责编:章丽